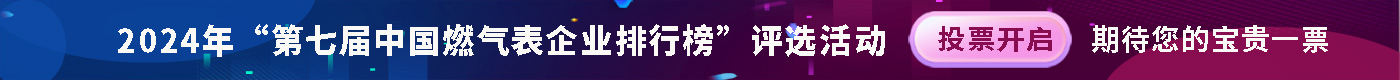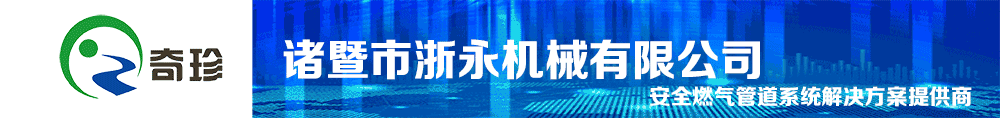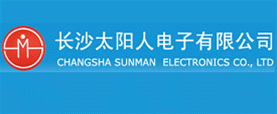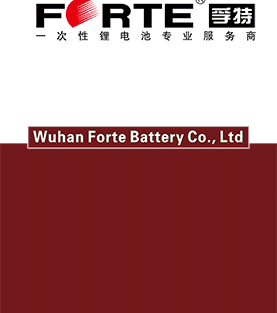各種新能源是否能夠滿足未來人類社會對于石油的饑渴?盡管國際能源署的一份報告描繪了這種可能性。
國際能源署即將于今年11月份發布一份《能源技術展望2008~2050年的能源情景與戰略》(下稱《能源技術展望》)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國際能源署試圖從技術投資的角度,為折磨全球的高油價問題尋找出路。
但是,國際能源署提供的解決方案并不被看好。
7月29日,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召開的未來能源發展方向與戰略的國際研討會上,國際能源署全球能源合作司中國項目主管喬納森·辛頓向他的中國同行提前介紹了這份尚未出爐的報告的主要內容。
《能源技術展望》根據未來國際社會對能源技術投資的大小,預測了三種有關能源與氣候危機的三種不同情景。
在第一種基準情景中,假設國際社會對目前的氣候變暖危機無動于衷,不采取任何的應對措施和技術手段,那么到2050年,全球的石油消費將會增加7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增加130%,全球平均氣溫將提高6攝氏度。
第二種情景是穩定型情景。到2050年應用現有的或正在開發中的先進技術能夠將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恢復到現在水平。這種情景的假設前提是,各種新能源技術已經得到廣泛利用。
第三種情景稱為BLUE情景,即在2050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2005年排放量的一半。這一誘人的情景并非毫無代價,它要求全世界需要增加45萬億美元的額外投資,用于新能源技術的商業化推廣和運營。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肯定了《能源技術展望》對中國的參考價值。“報告指明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由于氣候變化的原因,低碳技術是未來能源技術發展很重要的方向。”
國際能源署提供的后兩種情景基于相同的假設。它要求各種新能源技術的大規模、商業化的運營。包括CCS技術(碳的封存)、核能以及太陽能等,在2050年之前發生革命性的技術突破。
但是,李俊峰指出:“到目前為止,CCS技術還沒有一個真正成功的案例,連一個示范項目都沒有。”而且大規模的儲存碳,也面臨技術上的不確定因素。
此外,《能源技術展望》將未來能源的增量主要寄托于核電。尤其是在第三種情景下,國際能源署希望在2030年能夠實現大規模地應用新核能技術,并且在2050年核電能夠超過兩億千瓦。
“到目前為止,核電的推廣主要還是寄希望于第四代核能技術的發展,也就是快堆的發展,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不光中國沒有,全世界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李俊峰表示。
如果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增加對核能技術的研發投入。但是,全球的趨勢與此相反,多年來各國對于核能的研發資金持續壓縮。
國際能源署即將于今年11月份發布一份《能源技術展望2008~2050年的能源情景與戰略》(下稱《能源技術展望》)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國際能源署試圖從技術投資的角度,為折磨全球的高油價問題尋找出路。
但是,國際能源署提供的解決方案并不被看好。
7月29日,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召開的未來能源發展方向與戰略的國際研討會上,國際能源署全球能源合作司中國項目主管喬納森·辛頓向他的中國同行提前介紹了這份尚未出爐的報告的主要內容。
《能源技術展望》根據未來國際社會對能源技術投資的大小,預測了三種有關能源與氣候危機的三種不同情景。
在第一種基準情景中,假設國際社會對目前的氣候變暖危機無動于衷,不采取任何的應對措施和技術手段,那么到2050年,全球的石油消費將會增加7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增加130%,全球平均氣溫將提高6攝氏度。
第二種情景是穩定型情景。到2050年應用現有的或正在開發中的先進技術能夠將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恢復到現在水平。這種情景的假設前提是,各種新能源技術已經得到廣泛利用。
第三種情景稱為BLUE情景,即在2050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2005年排放量的一半。這一誘人的情景并非毫無代價,它要求全世界需要增加45萬億美元的額外投資,用于新能源技術的商業化推廣和運營。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肯定了《能源技術展望》對中國的參考價值。“報告指明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由于氣候變化的原因,低碳技術是未來能源技術發展很重要的方向。”
國際能源署提供的后兩種情景基于相同的假設。它要求各種新能源技術的大規模、商業化的運營。包括CCS技術(碳的封存)、核能以及太陽能等,在2050年之前發生革命性的技術突破。
但是,李俊峰指出:“到目前為止,CCS技術還沒有一個真正成功的案例,連一個示范項目都沒有。”而且大規模的儲存碳,也面臨技術上的不確定因素。
此外,《能源技術展望》將未來能源的增量主要寄托于核電。尤其是在第三種情景下,國際能源署希望在2030年能夠實現大規模地應用新核能技術,并且在2050年核電能夠超過兩億千瓦。
“到目前為止,核電的推廣主要還是寄希望于第四代核能技術的發展,也就是快堆的發展,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不光中國沒有,全世界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李俊峰表示。
如果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增加對核能技術的研發投入。但是,全球的趨勢與此相反,多年來各國對于核能的研發資金持續壓縮。